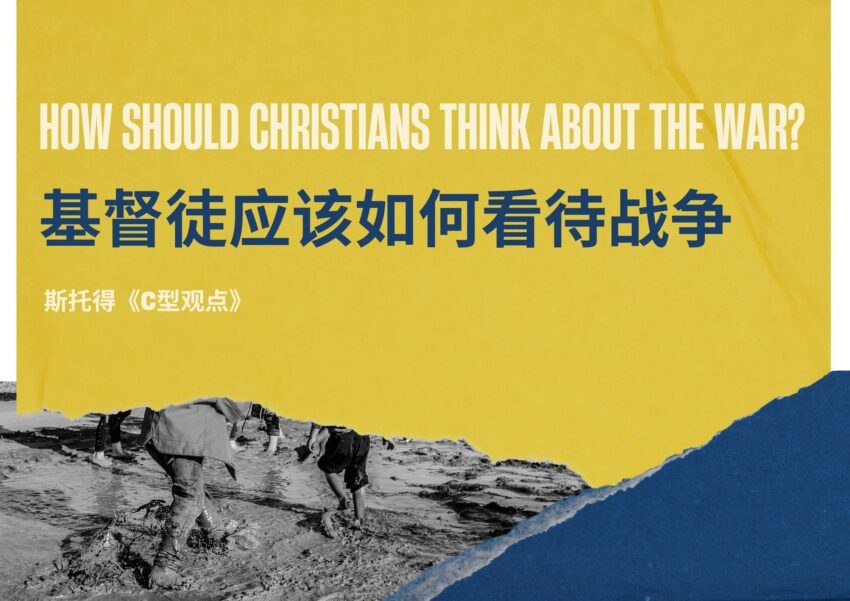本书节选自斯托得所著《C型观点》第四章
今日人类所面对全球性的问题,没有一件比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更严重。战争不再限于军队之间的冲突,一方面,好些国家已逐步发展出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,足以灭绝人类社会,甚至消灭整个人类文明;另一方面,我们看见恐怖分子团体大量增加,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,带著象征性,且威力十足。二十一世纪一开始,我们就非常担心,惟恐这两者凑在一起,一旦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——或是核子弹、细菌弹,或是化学炸弹——落到恐怖分子手中或流氓国家手里,便会被利用来达到他们的手段,而后果则不堪设想。
当然,即使是非常原始的武器,倘若使用的人充满仇恨,定意要消灭对方整族的人,也会造成惨不忍睹的杀戮。一九九四年,卢安达在一百天之内就有八十万人被杀,大多数是被大刀砍死;只要提到波士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(Srebrenica),就会让人联想到那里曾发生的惨事,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在「种族净化」的美名下被屠杀。
或许,近几十年最令人发指的事件,是发生在非洲刚果共和国(从前的萨伊)的内战,估计约有两百五十万人死亡,有些是直接因战争而死,有些则是由于疾病和营养不良。
所以,我们无需专门注意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,仍可以看见人间的冲突会带来何等可怕的灾难。二○○三年,由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发起的清除地雷国际运动估计,仍有一亿枚地雷留在地里,每年造成的伤亡达一万五千至两万人。因著更多国家组织清除地雷活动,而且安哥拉、斯里兰卡、苏丹相继停火,二○○二年地雷的减少令人鼓舞,但是二○○三年,地雷顾问团估计,由于一九九一和二○○三年两次的波斯湾战争,二十年来的冲突留下八百万至一千两百万枚地雷,由库德族(Kurdish)控制的伊拉克北部,由于地雷和其他爆裂物造成的伤害,在二○○三年的对峙后增加了90%。
再者,人类的冲突所带来最痛心的一面,就是把孩子牵连到战争中。死在武器作战中的孩子愈来愈多,三十万儿童军正在打仗,还有无数孩子担任后援,两千五百万名孩子因著战争而流离失所。女孩与残疾儿童最容易遭受摧残,一名儿童军描述他所经历的恐怖经验:「我埋地雷、拦下车子、烧房子、烧庄稼……,最让我难过的是,如果有孩子太累了,我们这些俘虏他们的人,就会奉命把他们杀了。」
现今我们已有能力,可以毁掉过去一切的文明遗产,摧毁目前地球生物的微妙生态平衡,而辐射线更可破坏未来的遗传潜能;因此全人类和这个星球能否继续生存,的确已成问题。基督徒思想不能流于空泛,无论我们多么坚信神透过基督和圣经的一次性自我启示,我们还是必须努力把启示与严酷的现况关连,由此,当我们寻求去分辨神的旨意时,启示与实况能环环相扣。有五方面的问题,我想先提出来,然后再谈基督徒在乱世中促进和平的呼召。
冷战的结束
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塌,世界的权力平衡改变,共产主义的理想分崩离析,苏联的军力开始衰退。苏联不再是全球的超级强权,她的国情快速改变,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领袖戈巴契夫(Mikhail Gorbachev)积极的洞察眼光,他带入「重新架构」和「开放」的概念,目的在为该系统带来某种程度的民主责任能力。但是还有部分原因是经济的贫困、政治的压迫,和苏维埃模式工业的落后,这些如同恶梦般困扰著政府。
一九八九年七月,由华勒沙(Lech Walesa)领导的波兰团结运动,在自由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。接著,戈巴契夫宣布,华沙公约中的国家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,匈牙利旋即向西方开放边界,捷克出现「天鹅绒革命」(velvet revolution),选出剧作家哈维尔(Vaclav Havel)担任总统。接著,经过些许流血冲突,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(Ceausescu)残暴的统治终告结束,他与妻子在圣诞节被处死。
尽管采取了新措施,苏联的经济继续衰退,戈巴契夫在国际上被视为英雄,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,但在国内的名声却愈来愈差。他只不过是苏联的总统,而不像他前面几任可以担任共产党的领袖,拥有新的权力,能采用强硬手段。当苏俄举行第一次选举时,选出的总统是戈巴契夫的头号对手叶尔钦(Boris Yeltsin),他废除了苏俄的共产党,强迫戈巴契夫解散中央委员会。一九九一年,四个苏维埃共和国投票选择独立,莫斯科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六日承认他们的主权,其他的共和国成员,乌克兰、亚美尼亚、乔治亚、摩尔达维亚,也都计划要脱离苏维埃。乌克兰、苏俄和白俄罗斯的领袖,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在明斯克(Minsk)聚首,同意将苏联解体,成立独立国邦联(CIS,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)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,戈巴契夫上电视,宣布辞去苏维埃总统职务,苏维埃旗帜从克里姆林宫降下,苏俄的旗帜升起,苏联成为过去。虽然这一切事没有来得及拦阻,一九五○年导致韩国分裂的美国和共产世界的激战,以及一九六○年代的越战,但是,二○○四年五月一日,大部分中欧与东欧前共产国家都加入了欧盟,还有两个国家,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打算于二○○七年加入(编按:此二国已于二○○七年加入欧盟);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改变是何等之大。
当民主的浪潮席卷前苏联,世界似乎将会更安全了,但是十年之后,和平的指望又成了泡影,新的冲突出现。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五这五十年之间,总共有八十场战争,然而其中只有二十八场是「传统」的战役,由国家的正规部队作战,另外四十六场则是内战或游击战。
暴力上升如此迅速,原因究竟是什么?哈佛大学的杭廷顿教授(Samuel P. Huntington)在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整》(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)一书中,发展出一个理论,认为冷战时期普世的政治是「两极化」(归于两大强权),冷战结束后,则变成「多极化与多重文明化」,尤其是「认同危机,对人而言,最重要的是血统与信仰,或宗教与家庭。人会与祖先、宗教、语言、价值观、习俗相近的人联结,而疏远与自己不同的人。」因此,今天人和人的差异,不再是理想、政治,而是文化。杭廷顿接著将世界分成七、八个主要的文明,其间最重大的差异是文化,而这正是造成「国家之间的对立或联合」的原因。
全球性的战争,就是世界主要文明大国都卷入的大战,杭廷顿教授认为「可能性不大,但并非全无可能」,他甚至生动地描绘,或许美国、欧洲、苏俄、印度会联手,对抗中国、日本和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。该书最后一句话为:「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,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,是抵挡世界战争的最安全防线。」不过我们要小心,切勿落入宿命论,以为这种冲突无可避免。九一一事件之后,有些人谈到「文明的冲突」时,似乎这是已经发生的事,这样的态度只会对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。
前联合国秘书长裴瑞兹(Perez de Cuellar)曾说,现今内战的增加是「新的无政府状态」,一九九三年,四十二个国家发生严重冲突,还有三十七国有较小规模的混乱,这似乎证实了「这股无政府风潮」。他说:「我们无法控制。有人以为,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精英可以从上面掌控大局,……这种想法全然错谬。」我们所处的是「各地皆有小型大屠杀场面的时代」。
自从冷战结束以来,世界局势有了极大的转变,毋怪乎,西方的国防专家已经将策略全盘修改。他们不再预备面向苏联,迎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,而是要应付多区域的冲突。不过,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依然存在,大家仍十分担心,惟恐有人在地方性冲突中使用,或是恐怖分子会疯狂地使用。以下便要思想这类武器。
大规模毁灭性武器
核子武器
当前拥有核子武器和运输系统的,共有七个国家:美国、苏俄、英国、法国、中国、印度、巴基斯坦,以色列几乎已是这死亡俱乐部的第八个成员。最近一位巴基斯坦核子物理学家表明,他已经将核子的秘密告知利比亚、伊朗、北韩,这几个国家是恶名昭彰的「流氓国家」,有些被美国总统布希列入「邪恶轴心」。
许多人认为可以不再理会核武问题(自然也不必去探讨其道德争议)。冷战期间美、苏对峙,两国各自拥有大量核武,核子大战彷若一触即发,而如今国际情势已截然不同,威胁不复存在。但这是一种诱惑,必须抗拒。二○○六年,全球国际关系最关注的焦点,即是伊朗已经制造出精炼铀,就是制造核武的原料,他们声称,这是用来提供核能,作为能源的一部分,但他们的核子计划却引起全球的关切。让人担心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伊朗新选出的总统艾哈迈迪-内贾德(Mahmoud Ahmadinejad)为极端的国家主义者,他呼吁要将以色列「从地图上抹去」;不过为公平起见,我们必须提及他曾经说过:「一个有文化、逻辑、文明的国家,不需要核子武器」。
未来既然可能出现极其骇人的景象,我们就不能遗忘上一次使用核子武器的时刻,也不能忘怀为何不能再度使用它们。核子弹爆炸的恐怖威力,或许亲眼目睹广岛和长崎惨况的报导,最能让人感同身受。蒙特巴登爵士(Lord Mountbatten)在遇害之前不久,曾引用过如下报导:
突然间,天空出现一道耀眼的白色、粉红色亮光,伴随著不寻常的震动,立刻便产生令人窒息的热浪,以及横扫万物的飓风。几秒钟之后,市中心街上成千的百姓,都被火烙般的热浪所烤。许多人顿时死亡,其余的人在地上蠕动,因著难忍的烧伤而痛苦地尖叫。凡爆炸之风所经之处,一切矗立之物……都化为乌有……。广岛已不复存在。
这只是一枚小型原子弹爆炸的情形。倘若核子战争发生,后果究竟会如何,实在难以逆料,因为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因素,诸如,会用多少弹头、目标地带人口分布的情形、民众可防御到什么程度,以及当时的气候如何。美国的国会文件〈核子战争的影响〉(1979年)提到,「最低限度的结果,也会极其恐怖。」
冷战期间曾提出许多场景分析,一旦两个超级强权以核子弹互相攻搫,后果会如何。例如,一枚百万吨威力的炸弹,若攻击像底特律或列宁格勒之类的城市,大约有两百万人会瞬间死亡,另外还有一百万人受伤;若「大规模攻击军事与商业目标」,前苏联先投弹,美国反击,则美国人会有77%(或一亿六千人)丧生,苏联则有40%(因多分布于郊区)。这些伤亡是当时随即发生的(三十天之内),由热度、爆炸、狂风、大火和直接的辐射所造成。更有千万人会死于受伤(因医疗设备完全不足)、传染病(由于下水道秽物四散,又没有清水供应),或在第一个冬天被冻死或饿死(因所有设备全毁)。一层厚厚的毒烟将笼罩被摧毁的地区,不仅令许多存活者中毒,也完全挡住了太阳的温暖和光,使地球重新回到冰河时期的状况。时日再久些,许多人会得癌症,而对遗传与生态的损害,则将历时数十年,影响无法估计。
生物武器
生物战争是故意散播疾病,如炭疽病、天花、肉毒杆菌毒或鼠疫。一九二五年日内瓦协定,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,一九七二年生物与有毒武器协议(BWC),废除这些武器的发展、制造、获取、屯积、保留,并于一九七五年起生效,然而,许多单位仍然制造这类武器。一九九二年苏俄总统叶尔钦承认,前苏联在过去二十年有生物武器的计划,令人益发担心有人会使用这些武器。一九九五年,曾经签署BWC的伊拉克,也被人发现有生物武器计划,后来有人发觉,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时,它曾使用含有生物成分的炸弹和飞弹。二○○三年兴兵攻打伊拉克的主要原因,正是怀疑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,而且准备要使用,结果,后来却遍寻不著。
生物武器需要一段时间才有效果,要看使用的材料为何,但是其强烈的普遍传染性却不可低估。国际旅行的速度意味,一种疾病可能在尚未查出病源之前,就已传播到其他各洲。
生物武器所以会受使用者的青睐,原因之一为造价相对便宜,「按分析,以传统武器造成一平方公里平民(未受到保护者)伤亡的代价为两千美元,核子武器为八百美元,神经瓦斯武器为六百美元,生物武器为一美元……?难怪生物武器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。」
与其他武器比较,生物战争也同样极其恐怖:「有一著名情节刻划,一架飞机经过华盛顿首府上空,从机尾顺著上风喷洒出一道一百公斤的炭疽病菌,会造成一百至三百万人死亡。相较之下,一个百万吨氢弹丢在美国首府上空,只会造成五十万至一百九十万人死亡。」
因此,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(Colin Powell)说:「让我最胆寒、比战略核武更可怕、我们更缺乏抵挡能力的,是生物武器。」这些武器不需要复杂的运输体系就可发挥作用,恐怖分子可以用车子、小飞机,甚至只要让载体迎风而上,就可发挥作用。有一次,日本奥姆真理教将一辆装有风扇的小货车驶到东京的街上,试图散播肉毒杆菌毒素,幸亏该次没有人受到伤害。九一一之后,这类攻击的可能性人尽皆知,还有人以相当专业的手法制作炭疽菌,透过邮政系统分送。不过,不少科学家不以为然,认为生物武器的运用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容易。尽管世事可能随时有变化,然而截至目前为止,生物战争还没有成为基地组织(A1 Quaeda)这类恐怖组织的手段。
化学武器
化学武器的作用,是以直接接触人的物质造成伤害或死亡,这种武器可以分为几类。「哽噎剂」,如氯气或光气,透过呼吸进入呼吸道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广泛使用;「起泡剂」,例如芥气,透过呼吸与皮肤的接触,影响眼睛、呼吸道和皮肤,起先奇痒,然后细胞遭破坏;「血液剂」,例如氢氰化物,是透过血液运送,一般是藉呼吸进入体内;这些毒剂主要是让身体窒息。还有「神经毒剂」,例如沙林或塔崩,会阻挡神经细胞或神经原之间的感应。这些毒剂又分为几类,最广为人知的是CS催泪性毒气,防止暴动的单位常用到,而最为致命的,如VX毒气,只要几毫克就足以夺命。
一九八九年,约一百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开会,商讨废除化学武器。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,化学武器协定生效,有一百一十七国签名,这是世上第一个多国废武协定,为要在所定的时间之内削减一系列大规模毁灭武器,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(OPCW)的成立,便是要监督这件事的执行。
倘若这件事真能成功,便是完成了从一六七五年便开始推动的事,当时法国与德国共同斥责子弹上毒,并禁止其使用。一八七五布鲁塞尔会议禁止使用有毒气体与武器,一八九九年海牙协定禁止可以散播「造成窒息或伤害之毒气」的发射器,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化学武器被大量使用,最恐怖的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比利时的伊珀尔(Ypres)战役。战事结束时,氯气、芥气和各种化学毒剂总共释出十二万四千吨,受到折磨而死的兵士达九万名以上。
这大大违反了海牙协定(Hague Conventions)。一九二五年日内瓦公约规定,签署国(现今几乎包括所有的国家)不得率先使用这类武器,第二次世界大战时,签署国没有一个违反承诺,不过义大利曾在一九三○年代在阿比西尼亚(Abyssinia)用过化学武器。此外,「黄雨」的传闻也让许多人认为,苏联军队曾在阿富汗使用毒气,而共产党军队也曾在柬埔寨和寮国用过。伊拉克在攻打库德族和与伊朗作战时,一定也用过。
然而,我们的问题还不止于有些国家会用化学武器。一九九五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放置沙林毒气,造成十几个人丧生、五千五百人送医。该沙林毒气已经稀释成只有三分之一的威力,以保护置毒者,倘若它具百分之七十的纯度,会让上千的人死亡。该事件显示,尽管尚未有团体使用它们来造成大量的伤亡,然而恐怖组织使用化学武器已成为事实,许多分析家相信,假以时日,必定会有人这样作。
同时,一般民众必须了解,现代神经毒气对化学家而言,就像核子武器对物理学家一样。防毒面罩可能无法提供保障,因为有些化学武器可以穿透皮肤,倘若是从空中投掷,估计平民与士兵的死伤会是二十比一,因为只有士兵会穿具防护性的衣著。
核子、生物及化学武器有时被合称为「ABC」武器(atomic, biological, chemical),这诚然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字母组合。对战争道德问题的思考,由于ABC武器的发明与精炼,尤其是核子武器,情境已经完全改变了,它们改变「公义战争」理论的中肯性,一场战争可能有其公义的理由与公义的目标,但是,倘若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(「战略性」或「战术性」),就无法期待人持守目标,因为以核子战争而言,最终不会有任何人赢。手段不可能公正,因为核子武器不会按比例施放或作出分辨,也无法控制。千百万平民百姓会丧生,在核子屠杀中,无辜之人必然血流成河。所以,基督徒的良心必须宣告,使用无分辨力的核子武器,以及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,都是不道德的,核子战争永不可能是公义战争。正如一九八五年,雷根总统与戈巴契夫先生于日内瓦所宣示,「核子战争不会有赢家,也永远不该发动。」
神学与道德反思
对于战争,基督徒之间一直没有定论,恐怕也永远不会有,然而我们不应该夸大彼此之间的不同,也不要低估我们的相同之处。例如,所有基督徒都肯定,耶稣所开始的神的国,乃是神以公义与和平治理的国度,耶稣的所作所为,成了祂所宣扬之国度的完美榜样;属神国度的团体要渴慕公义,追求和平、不求报复、关爱仇敌,换言之,是要以十字架为记号;在国度成全时,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,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;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」(以赛亚书二4)
这一切乃表明,我们既是基督徒,就必须力求和平与公义,以公义来追求和平,比讨好人要付更大的代价,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便有亲身的经历。我们也称许军人的忠诚、牺牲与勇气,然而,无论从事战争的理由多么严正,我们也不应当推崇战争本身。有些基督徒相信,在某些情况下,它是两种罪恶中(犯某一罪以阻止更大的罪)较轻者,但在基督徒的思想中,它最多只不过是堕落世界中一种必会有的痛苦。
虽然按照圣经,大致可整理出以上原则,但基督徒中间有三种不同的立场,各有各的理由:公义战争派、全然反战派及相对反战派。
「公义战争」的传统
「公义战争」的概念,始于基督徒时代之前,可以追溯自旧约的「圣战」,以及一些希腊、罗马的伦理教导。第四世纪时,奥古斯丁将这个观念纳入基督教;十三世纪时,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又将其系统化;到了十六世纪,维多利亚(Francisco de Victoria)予以发挥,而大多数改革教派亦赞同。今天大部分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会都持此立场。公义战争的传统通常会提到七项条件,才可算一场合乎公义的战役,即:正式宣战、最后手段、理由公正、动机正当、方法得当、不伤平民、合理期待。不过,这七项标准有重复,我觉得减为三项较清楚,即战争的开端、行为与结束。
那么,我们怎样判断一场战争是否「公义」?
首先,理由必须正当。是出于防卫,而非主动攻击,目标须为保卫公义或补救不义、保护无辜或保障人权。只有在一切谈判、和好的努力皆无效,别无其他选择时,才能进行,并且要经由合法政权正式宣战(先下最后通牒),不能由个人或团体任意发动。此外,动机也要与理由同样公义,正当的理由不能为不公义的动机所利用,因此不能有仇恨、憎恶或急欲报复的心。
第二,方法须有控制。不能恣意使用暴力,也不能滥用。有两个词曾用于形容正当暴力的运用,一为「按比例」,一为「分辨」。「按比例」意指,战争乃是两种罪恶中之较轻者,所承受的暴力,在比例上而言,比那要补救的事少,最终则利多于弊。「分辨」乃指,战争是针对敌军的作战部队与军事目标,不波及平民。我们必须承认,平民绝不可能完全免受扰害,但在「公义战争」中,必须作此区分,而视故意杀害平民为违法。在海牙协定(1899、1907年)中,不波及平民的原则已隐含在内,到了日内瓦会议,及后来的补充公约(1949、1977年)中就明文规定,联合国大会则更再度强调(1970年)。
第三,后果须可预料。耶稣曾讲过一个简短的比喻,一位王在出征之前,必须「计算代价」(路加福音十四31~32),因此战争必须有胜算,并能达到发动战争时的正当理由。不过,有时候一个国家可以为了原则性的理由而战,即使它觉得仇敌更有力量,自己所冒的险很大,有些人或会以为,英国在二次大战时为了实现条约的义务而投入战争,便是如此。然而,若没有合理的胜算便去作战,乃是愚昧的,也将使千万百姓牺牲性命,而他们的生命并无法换来要达到的目标。
总而言之,「公义战争」是为正义而战,用节制手段,并有合理胜算的战争。
不过,「公义战争」理论只是一种传统,它是否有圣经的支持?有些人试图以旧约为证,指出有些战争是耶和华所命令并指挥的,但这个讲法很危险,因为那些战争明显是圣战,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当日的以色列,享有特殊地位,作「圣洁的国度」,神所特别立约的子民,由神亲自治理。
另外一个基础较稳固,是依据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1~7节及其上下文对政府的教导。其实该段圣经的前后,是论爱邻舍,前面教训我们要爱仇敌、服事他们(十二14~21),后面说明,爱是不加害与人的(十三8~10)。因此,我们在解经上遇到很大的困难,尤其,罗马书十二章的结尾和十三章的开头似乎互相矛盾。前者回应了登山宝训,禁止我们以恶报恶;后者则似乎在回应旧约,认为政府是神的工具,为要刑罚恶人。前者说,恶人要给予服事;后者说,要刑罚他们。这些教训如何能调和呢?
使徒保罗肯定政府的权威是由神所设,祂授权给他们,因此,顺服政府就是顺服神,违背政府就是违背神;再者,「在上有权柄的」(任何政府官员)都是「神的用人」,要奖赏良民,刑罚恶人。其实,保罗三次重复提到,政府的「权柄」是神的权柄,又三次提到,政府的「工作」是神的工作(罗马书十三4a、4b、6)。我认为这里很清楚,神并非不得不为有罪的政府「安插」一个特权的位置(在他们用武力罚恶时,仍算「犯罪」);相反的,乃是肯定神已经「设立」政府,将祂的权柄赋与他们,他们运用权柄去罚恶,便是执行神的旨意。既然如此,我便不能主张基督徒远离公职,反而要鼓励他们参与,知道他们这样做乃是成为「神的用人」,就像牧师一样,因这名词也同样用在牧师身上。基督徒担任警察、典狱长、政治家、市长、议员,绝非不正常,因为基督徒所敬拜的神是公义的,因此他们也要追求公义。基督徒团体不应该远离世俗社会,而应当努力为基督渗入其中。
大部分的反战派人士(不包括主张和平之教会的人)都接受基督徒参政的立场,不过,他们也像其他基督徒一样,是在必要时,有条件性地参与,例如,他们会拒绝国家的征兵令。
那么,罗马书十二章17~21节要服事仇敌,和罗马书十三章1~7节要刑罚作恶者,这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差距,我们如何解决?如果我们注意到赦免与刑罚的矛盾,不仅存在于这两段经文之间,也包含在前者之内,便会开始明白答案为何了。因为「不要以恶报恶」的禁令,下一句是:「主说:我必报应」;而「亲爱的弟兄,不要自己伸冤」的禁令,下一句即为:「宁可让步,听凭主怒;因为经上记著:『主说:伸冤在我,我必报应。』」(十二17、19)因此,我们不可以发怒、报复、还手的原因,并非这样对待罪恶是不对的,而是因为这是神的特权,而非我们的权力。同样,耶稣虽「被骂不还口」,但也「将自己(及所面对的事)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」(彼得前书二23)
所以,最好的解释,是视罗马书十二章末尾与十三章开头相辅相成。神的新团体之成员,可能兼有个人与政府官员的角色,在前一角色中,我们不可自己报复,或以恶报恶,反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(十二14)、服事仇敌(十二20),并尽力以善胜恶(十二21);然而,就后者的角色而言,若我们蒙召是要作警察、狱吏或法官,我们乃是神罚恶的代理人。当然,「伸冤」与「忿怒」都属于神,但祂今日刑罚恶人的途径,乃是透过政府,故「听凭主怒」(十二19)意为,让政府作「神的用人,……刑罚那作恶的」(十三4)。这不是说,执行公义时不可顾到怜悯,其实正该如此。政府官员不仅应当「刑罚」罪恶,更要「胜过」它,因为刑罚与改造应当并行。不过,这段圣经所强调的乃是,倘若罪要受罚(理当如此),则刑罚要由政府和其官员来执行,不容个人以自己为律法,任意而行。
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,政府的刑罚角色受到限制,也有节制。罗马书十三章1~7节绝不支持高压政权,对它们而言,「法律与秩序」即是暴力统治的同义词。政府是神的用人,执行祂的忿怒,只对作恶的人而已,即对特定、作错事、需要秉公处置的人。这意味对政府的权力有三重限制:第一,政府所刑罚的人必须是作恶、犯法者:第二,逮捕他们的武力,必须为把他们绳之于法的最低需要:第三,所给予的刑罚,应该与他们所犯的错相称。这三件事——人、武力、刑罚——应该谨慎掌控。
同样的原则不但可以用于警察,也可用于军队,其实,这两者的区分乃是近代的事。今日警察所做的事,如执行法律、维持秩序、保护无辜等,在保罗时代乃是罗马兵丁的责任,现代某些国内的动乱(如,肯亚毛毛族的叛乱),仍会动用军队来支援警力;在这类情况下,士兵的行为应当视为警察的延伸,不能越轨。例如,英国国防部长解释,现行有关维持安全的法律,当以「『所需最低限度武力』一语来标明」、「根据状况的需要,使用合理武力,不得滥用。倘若所用的武力,超过当前欲达到的目的,便为不合理」,武力主要的目标在防止犯罪,以及逮捕犯人。
然而,如果扰乱和平的不是个人或团体,乃是另一个国家,则又如何?这时论点为,按合理比例扩大来看,神所赐给政府执行公义的权柄,包括约束、抵抗那些作恶的人(在此情况下是侵略者,而非罪犯),以保护其公民的权益,无论是外国的侵略,或本国的叛乱都一样。当然,这个类推并不尽然相符,因为一方面,作战的政府成了自己个案的审判者,而不是作仲裁的第三者;另一方面,法庭冷静、按部就班的审理,与战争的宣告与进行截然不同。这些差异是由于目前被接受的国际公义(在仲裁、介入及保持和平方面),只在婴孩阶段,不过,「公义战争」理论的发展,「代表一系列的努力,要将战争行为与政府行为作类比」,务期使之隶属于「执行公义的范畴」,并受「执行公义的标准所约束」。
然而,无论在罪行、暴动或国际战争中,要执行公义,首先必须是分辨性的行动(清查参与犯罪、须受制裁者),且是受到控制的行动(限制所用的武力,为达成目的所需之最小程度)。
委身于反战
在这个核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的时代,反战主义(pacifism)可能是全然反战,或是相对反战(有时称为反核战主义)。以下先谈全然反战主义。
全然反战的立场
反战派多半以登山宝训为出发点,至少许多人决心不介入暴力,是依据耶稣的这段教训。耶稣说,我们不要抵抗恶人,相反的,如果他打我们的右脸,我们还要转过左脸来由他打;我们要爱仇敌,向恨我们的行善,为逼迫我们的祷告,惟有如此,我们才配作天父的儿女,因为祂的爱普及众人,赐日照、甘霖给好人也给坏人。恨那爱我们的人,是魔鬼的作法;而爱那爱我们的人、恨那恨我们的人,是世界的作法,倘若我们要跟随耶稣,接受祂国度的标准,就必须爱那恨我们的人(马太福音五38~48;路加福音六27~36)。
不但如此,耶稣还身体力行。祂以身作则,不用暴力,在被出卖、逮捕、受审、定罪、折磨、钉十架的过程中,祂毫不反抗。受羞辱时,祂不还口,祂是神那无辜、受苦的仆人,「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,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,祂也是这样不开口。」(以赛亚书五十三7)祂爱那些藐视、拒绝祂的人,祂甚至为钉祂于十架的人祈求饶恕。
因此,反战人士下结论说,耶稣的教导和榜样,都要我们采取不抵抗、非暴力的立场,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,耶稣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祂。此外,历史似乎也可作证,在君士坦丁归主之前的两个世纪,大多数基督徒都拒绝当兵;不过有明显的证据指出,他们的拒绝与罗马军队中拜偶像的作法有关。反战派则辩称,他们也认为战争与顺服基督相违。这一点却无确据。
采取反战立场的,在十六世纪有被称作「极端改革派」的人士(各种重洗派),今日则有「和平教会」(Peace Churches;贵格会、门诺会、联合弟兄会等),还有不少较小的「历史性」改革宗教会。
相对反战或反核战*{Decide for Peace, Evangelicals against the bomb,此书为Dana Mills-Powell所编,是十六篇反核战与反战的评论集(London: Marshall Pickering, 1986)。}*
核子武器的发明,使战争的辩论展开新的一页,传统看法所探讨的旧范畴,似乎像传统战争中的旧武器一样,被弃置不用。科学家和神学家都提出呼吁,需要新而大胆的思想,正如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在第二次梵谛冈会议时所说,教会必须「对战争作彻底的重新评估」。因为每个人都知道,一旦发生核子战争,伤亡将达千百万,也不会只限于双方的军队(过去大致是如此,不过本世纪已有扩大现象)。
我们应当思考、应用的相关圣经原则,似乎是「流无辜人之血」的大罪。圣经看重「血」,因它是生命所赖,也是其象征(如,创世记九4;利未记十七11;申命记十二23),因此,「流血」乃指以暴力夺去性命,换言之,就是杀人,但是人的生命既按著神的形像所造,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旧约时代严禁流人的血,除非有神特殊的许可,即处死杀人犯,和在神所授权的战争中。不错,在摩西五经中,还有一些严重的罪(如:绑架、咒诅父母、行巫术、与兽淫合、拜偶像、亵渎,见出埃及记二十一、二十二章及利未记二十四章),要处极刑。但最高的原则为:「凡流人血的,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」(创世记九6)亦即,谋害人命、流人血,当流血处死,因为后者之血是有罪的血。除此之外,则都是「流无辜人之血」的罪,所以,亚比该因大卫没有亲自向拿八报仇而感恩,他「不……流无辜人的血……必不致……觉得良心有亏。」(撒母耳记上二十五31)
旧约设立六座「逃城」,就是为贯彻这个教训,约旦河两边各三座,位置都经过仔细考虑,涵盖全国。其根据为将谋杀(蓄意杀害)与误杀(非故意)区分出来,并保护误杀人者,以免被「报血仇者」所害,而流无辜之血(民数记三十五9~34;约书亚记二十1~9)。
旧约时代不仅区分谋杀与误杀,还区分战争时的流血(是许可的),与和平时的流血(不许可)。因此,约押杀害押尼珥和亚玛撒这两位以色列的将领,大卫定他有罪,因为「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,如在争战之时一样」,以致令大卫家犯了流无辜人之血的罪(列王纪上二5、31~4)。
因著旧约有这个律法,先知们向以色列发出猛烈的斥责。耶利米警告他们,神必将刑罚他们,因为他们离弃祂,玷污了耶路撒冷,怎么回事?原来他们「在这里向素来不认识的别神烧香」,又「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」(耶利米书十九4)。此处将拜偶像与流血并列,对神而言,最严重的罪莫过于拜偶像,对人而言,则是流无辜人之血。以西结也同样指出,耶路撒冷自寻灭亡,因「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」,又「作了偶像」(以西结书二十二1~4,参三十六18)。这两位先知都将偶像崇拜和杀害无辜视为最重大的罪。
新约也同样极端厌恶流无辜之人的血。犹大承认,他「卖了无辜之人的血」(马太福音二十七4);彼拉多声明:「流这义人的血,罪不在我」,而百姓鲁莽地回答:「他的血归到我们,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」(马太福音二十七24~25)
圣经对这件事的看法始终如一,从列祖时期,到律法、先知时代,以至新约皆然,令人印象深刻。人血神圣不可侵犯,因为它乃是像神之人类的生命,故此流无辜人的血是最严重的社会罪行,无论是个别的谋杀,或是高压政权的依法处决。神的审判于主前第七世纪临到以色列国,因为他们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;又于第一世纪临到他们,因他们流了耶稣基督的血。耶和华所恨恶的事中,「流无辜人血的手」为其一(箴言六16~17)。
圣经的这个信息不能置之不理。神赋与政府的法定权柄,包括用「剑」(罗马书十三4),都有严格的限制。对警察而言,只有在逮捕犯人、使他们伏法时,才可使用;对军队而言,只有在从事公义战争、用公义方法、达公义目的时,才适用。因此,任何无限度、无节制、不加区分的武力使用,都当禁止,尤其在战争时,战士与非战士、军队与平民,总是分得一清二楚。当然,军队也是由按神形像所造的人组成,他们或许被征召入伍,并非出于自愿,而且他们或许完全没有参与政府所犯的罪。不过,既然抵挡侵略国是合理的,视军队为国家代理人,所以不包括百姓,也是合理的;这种区分为国际法所认可(在战争时需保护平民),也有圣经根据(禁止流无辜人之血)。这可以应用在两方面。
第一,非士兵的豁免原则,谴责「传统式」武器(即非核武)的滥用。例如,基督徒的良知反对一九四二、一九四三年「毁灭式」、「地毯式」地轰炸汉堡、科隆及柏林,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对德斯登(Dresden)的轰炸。英国和美国的领袖(主要是邱吉尔和罗斯福)从前曾指责纳粹轰炸各城的作法可憎可怖,英国政府也曾公开宣称,它绝不参与轰炸非军事目标的决策,不论纳粹怎样行。但是同盟国收回承诺并保留这样作的权力,以防范德国不遵守同样规定。一九四三年同盟国轰炸汉堡,一九四五年轰炸德斯登,造成「火风暴」,其恐怖无法想像。据估计,一九四五年二月两天的轰炸中,死了十三万五千人(比落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,立即毙命的人还多);其中包括成千在苏联进攻之前逃避的难民。我个人很感佩奇彻斯特(Chichester)的贝尔主教(George Bell),他有勇气在上议院抗议这个政策。他说,毁灭式的轰炸「不是公义战争的行为」,而「要为不人道的方式辩护,强解为权宜之计,就无异于受了纳粹哲学的污染,以为强权就是真理。」圣公会教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〈教会与原子弹〉(The Church and the Atom, 1948年),与他的判断一致,认为德斯登的轰炸,「与公义战争须受限制的目的相背:它违反了分辨性的原则。」
第二,非士兵的豁免原则,也谴责使用无差别武器。我在本章前文中已经讨论过核子、生物和化学武器,爆炸时都不具分辨力。基督徒对这件事的看法,似乎日趋一致,第二届梵蒂冈会议说:「任何一种战争行为,若不加区分而摧毁整个城市,或一大片地区,以及其中的居民,便是得罪神、得罪人,应当立即定罪,且清楚定罪。」 一九八○年十一月,圣公会大会论及核子武器,说:「使用这类武器,与所谓公义战争的要求全然不符。」
对于其他教派的圣经观点,福音派基督徒一向很慢才知道,不过,一九八○年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(福音派的参与者不少)在美国聚集,他们认为,二十世纪有废止核子武器运动的需要,就像十九世纪废除奴隶的运动一样,因此发表了「新废止约定」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「核子武器的暴力没有限制,对受害人不加分辨,毁灭的范围无法控制,已将人类带到十字路口。历史中从未有一时代像现在一样,面对和平或毁灭的抉择。在核子战争中,绝无胜利者。」 这些基督徒宣言对核子武器的评价,也同样适用于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,因为这三者都不具差别性,无法为其使用辩解。
因此,各地的基督徒和所有渴望和平的人士应当联手,推动废除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。美国与前苏联减少核武之后,这件事已有长足的进步,但是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仍有核武,而他们又为与喀什米尔相关的事不断发生冲突。这便意味,虽然我们在冷战时期最害怕的末世性恐惧已经降低,但在现今的世界,核子武器的威胁仍旧非常真实。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亦是如此,生化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日形重要,新的科技大多是为了要治疗身体,但也可能成为破坏身体的有效办法,这个难题似乎很不容易解决。我们愈多发现身体的作用,便愈多倚赖发现者的善意,才能将其发明作有益于人的用途,而不是用来制造更有效的武器。全世界协力采取行动促进和平,其重要性在这个时代无可言喻。
问题与条件
然而,如果我们要面对这真实的世界,我还想到四件事,是必须要谈的。
区分士兵与平民
士兵与平民的区分是否已经过时?亦即,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战争,没有所谓的非作战者。全国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其中,为战争而努力。每一个纳税人都在资助战争;甚至从事一般工作的人,也是让别人因此而入伍。所以,既然人人都参与,使用无差别性武器,不就很合理吗?
要回答这问题,我们必须承认,将一个国家和其中专事作战的一小群军队作清楚区分,这是旧观念,如今已不适用;而每一个参与制造、运输或使用武器的人,都当视为作战者。不过,还是有少部分人,如老人、孩童、身体或精神有病者,他们绝对是非战士,应当受到保障,若杀害这类人,便显然是流无辜人的血。
旧约全体毁灭的例子,并不是恰当的类比,因为那里特别告诉我们,该地已恶贯满盈,因此,并非是「无差别」的审判。在洪水之前,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,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」(创世记六5);如果所多玛、蛾摩拉有十个义人,便可免于毁灭(创世记十八32);迦南人的习俗非常堕落、可憎,以致土地要「吐出它的居民」(如,利未记十八25)。
如果,旧约全体毁灭的审判不能作无差别之战争的先例,那么,旧约全体担当或负责的原则又如何?神曾论自己说,对恨祂的人,「我必追讨他的罪,自父及子,直到三、四代」(出埃及记二十5);而耶路撒冷被毁之后,存活者受到极大的羞辱,他们埋怨说:「我们列祖犯罪,……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。」(耶利米哀歌五7)神这样作,是否意味我们在战争中也可以伤及无辜?不!这里所展示的原则,是神视其子民为一个国家,我们不能将其转移成必须列举其罪状的法庭状况。因此,倘若「公义战争」要成立,只有一种可能,即视之为按公义治理的延伸,那么,无论如何总要将无辜者与有罪者区分出来。
有一件重要而让人不安的事值得一提,即使在区域性战争和内战之中,士兵与平民的区分也常未见遵守。反对武器买卖运动(CAAT)曾宣称:「自一九四五年以来,千百万人已经死于战争。到一九九○年代末,战争的受害者几乎百分之九十是平民,其中至少一半是儿童。」
虽然,我们可能距离战争场面很遥远,但无辜之人被屠杀应当会令我们义愤填膺,不可以视若无睹,推说这种事在战争中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们必须重拾同情之心,去体会无辜之人为自己的性命忧心忡忡,和无缘无故遭受虐待的心情。面对这类邪恶的张狂,我们的抗议显得何等苍白无力,但是,在感动之下采取行动,必定会让我们觉得,作一点事总比什么都不作要好。写信给媒体说明情况以唤起注意,打电话给选区代表,要求在国会提到这事,或参加某个在这些国家中积极提升人权的人权协会,都可能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。在战争可能爆发的地方,调停工作或许能防止悲剧,因此,当大火即将点燃时,基督徒调停人必须投身去化解。不过,除了作这些事之外,基督徒也蒙召要祷告;要祷告,因为我们相信祈祷会改变世界,因为这是与神的旨意同工的行动,神乃是公义的神,祂关心无辜者的权益。
区分差别性与无差别性武器
有人指出,并非所有ABC武器都是无差别性武器。例如,有些化学武器在战场上的使用,可以相当受控制,有人甚至建言说,核子武器已作到非常精密的地步,可以异常准确地击中目标;而改进的辐射武器或「中子弹」,可以藉杀死一辆坦克车内的士兵来拦阻它。因此,既然武器的研发朝向缩小目标、准确命中,核子武器便更具差别性,不必将其运用完全推翻。这便是他们的论点。
这个理由显然有些说服力,武器愈具无差别性,就愈无法令人接受。因此,可以想像在某种情况下,使用很有限的核子武器或许是合理的,虽然还会有某种程度的辐射外泄,造成一些平民的伤亡,但这必须是在绝对紧急的状况下,否则,就会被邪恶的强权征服,而那会导致更大的罪。
在冷战时期,两大超级强权互相对峙,各自拥有核武,问题是一旦有一方使用核子武器,战事便会升高。不过,在苏联解体之后,就不再有两大强权对立、各自拥有为数可观之核武的状况了。现在让人惧怕的,是核子科技流通出去,某个流氓国家会用一颗核子弹来颠覆某个地区或攻击其敌人,而该敌人或有核武可还击,或没有。倘若伊朗制造了一颗核子弹,中东遭破坏的可能性便立刻告急,尤其以色列亦有核子武器,即使只用有限的核武,在中东的弹丸之地亦必带来毁灭性的破坏。就武器本身的威力而言,或许可以视为是有限的,但若以为这种武器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亦是有限的,就太过天真了,一旦互相发射任何一种核武,要预期或控制接下来的进展,几乎根本不可能。
区分武器的使用和拥有
倘若使用ABC武器是罪,那么保持核武作吓阻之用,岂不同样可视为罪?假定我们同意,既然巨型核子武器造成不分辨的破坏,其使用便为不道德,而微型核子武器也有促进战事升高的极大危险,故其使用亦不合理,那么岂不是意谓,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委身于片面裁减核子军备?其实不然,并非所有相对反战(或反核战)者都主张片面裁军。因为就道德而言,拥有、威胁和使用是不同的。某种行为假如是不道德的,而威胁要如此作,也同样不道德,这个说法或许正确,但是拥有核子武器只是一种警告,而不是攻击的威胁。其实,因拥有的动机不是要鼓励使用,而是要防止使用,拥有便不应当像使用一样视为有罪。
那么,我们是否指斥使用,而为拥有作辩护?这似乎是我们的结论,当然,我们立刻可看出,其中的逻辑有问题。因为有效的吓阻在于有必要使用吓阻时的技术(科技能力)与意愿(道德与政治),也在乎敌人相信我们会这么作。因此「保持拥有,拒绝使用」,虽然在道理上讲得过去,但实际上却似乎在自打耳光,我们的矛盾在:吓阻无效或不道德只能择其一,或说,若要站稳道德就必无效,而若要有效吓阻(会使用武器)则必不道德。亦即一边是原则,一边是深谋远虑;一边是对错,一边是实况。潘能柏格教授(Wolfhart Pannenberg)针对这个矛盾写道:「这个冲突……是两种不同的伦理态度:一种伦理为坚守信念,即持定纯净的道德原则;另一种伦理为责任感,觉得必须考虑作出决定后会导致的结果」。
不过,就我个人而言,我不愿意被迫在基督徒的理想和基督徒的实际中作一选择(如果可以宽松地使用这些名词的话)。反核战人士自然是理想主义者,他们看得很清楚,坚持认为使用无差别毁灭性武器并不道德,拒绝在此原则上妥协。但是在把持这理想的同时,我们也必须面对这堕落世界的罪恶,以及其在时局中的反映。那么,应当如何协调理想与实际呢?上述「使用则不道德,保有则为审慎」的两难问题,是否有任何出路?在思考这点时,有五方面需要纳入考虑。
吓阻与裁军的平衡
我接受立刻片面裁军,特别就核子武器而言,反会促成核子战争,而非减低其可能性的论点。敌人可能会受到诱惑,利用我们自己造成的弱势,或许在不怕报复之下使用核子飞弹,来迫使我们投降(这样,我们便是因戒绝自己的使用,而促成对方的使用);或许会藉使用它们而来胁迫我们(这样,我们的不用,等于鼓励敌人来接管)。问题乃是,怎样才能阻挡双方使用核子武器,同时又保持我们的自由?所以较安全的办法,也是与理想和实际都符合的办法,就是一方面保持核子吓阻力,一方面寻求如何才能达到双边裁军,且要能持续进行,又是可核实的。
吓阻是朝向裁军的暂时步骤
保持吓阻武器(这类武器若使用则不道德)惟一合宜的理由,便是视为暂时的权宜之计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八二年六月,在联合国第二次特别裁军研讨会说,核子吓阻「以现在作判断,在道德上尚可接受」,但必须视为「本身不是目的,而是迈向逐渐裁军的一步」。 在寻求有效裁军之途的过程中,这一点应当更能增加紧迫感。
「大胆的和平表态」
在双边裁军的架构下,还有余地可容主动而有创意的片面裁军,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称之为「大胆的和平表态」(Audacious Gestures of Peace)。早先西方曾作此表态而未得回馈(如,美国一九七九年自欧洲撤除一千颗核子弹头,不过,这些当然是过时之物),然而这类行动可以做更多,而还不致产生危险。无论可能的敌人是谁,我们都应当有勇气,宣告定意「不先使用」。
充分而非超越
不论我们的良心是否能接受,核子武器可分成有限度与无限度,我们都应该可以同意,后者当禁用、废除。例如,伍德教授(Keith Ward)认为,根据道德原则,我们可以「犯某一罪(产生伤害)以阻止更大的罪」,因此主张,在极端状况下,使用有限度的核子武器是两罪之中较小者。不过他宣称:「全面的核子战争,必须严加定罪,……这在道德上是说不通的。」他又说:「必须拆除可进行全面核战的一切装置」,只维持「有限度的核子吓阻力」,即吓阻的最低需要量。核子武器量的「超越」完全不必要,核子的「充分」就已足够。再者,由于强权目前的军火可大量「过度杀害」,大量减低库存也似乎不构成难以接受的冒险,而这种裁减可能成为推动力,加速两边的裁军。
可信但不确定
同时,吓阻力也应当维持可信度。倘若核武的使用是不道德的,我们就不要威胁说要使用它,可是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吓阻,也不能只是虚张声势。惟一的选择似乎是培养不确定的气氛。我们可以向敌方说:「我们认为,使用无差别毁灭性武器是疯狂而不道德的行为。我们决定不要使用,我们相信你们也不愿意使用。可是如果你们攻击我们,或许会激起我们作出违反我们的理性和良心的举动。请你们不要把我们逼到那个立场。」
区分征服与杀灭
敌军的全面征服难道不是比核子战争更大的罪吗?最常被假想的一幕,也是最令人害怕的情形,便是入侵的军队拥有非常优越的传统武器,而我们与同盟国在面对失败的威胁时,受诱惑而决定以核子武器自卫,结果使世界卷入核子战争。人们问我:「这样作是否不合理?」我们能否认真假想容许国家被征服的情形?如果我们预期最坏的状况会发生,那么,我们所拥有的自由,就是我们认为生活品质中不可缺少的质素,会遭残暴压抑。这种罪恶是否真正「无法忍受」,比核子战争的破坏更糟?当然,犯征服之罪的应当是无神的侵略者,而非我们。可是,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某些合理的行动来避免此结局,而我们却没有采取,我们就成了帮凶。如果可以做而不做,那「不做」就成了犯罪。从另一方面看,倘若为避免被征服,而「可做」的事是决定从事核子战争,就又回到原来的问题:究竟哪一种罪更大?
然而,反核战者所关心的是道德原则,而不是机巧的平衡。我们的立场乃是:发动(或参与发动)核子战争,是极其大的罪恶,没有任何一种理由可为其辩护,甚至连我们害怕被征服或被毁灭,也不成理由。若必须生活在高压政权之下,承受一切痛苦与奴役,岂不仍强过毁灭人类文明的罪?容许千万人丧失自由,固然是件恐怖的事,但为防止此事的发生,我们岂准备让千万人化作灰烬?我们自己忍受不公义,岂不是比加在别人身上更好?
因此,最后我们要决定,哪一种祝福是我们更看重的:社会自由——因此而发动核子战争,以致失去道德的正直;还是全国的道德正直——虽然必须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,让别人征服我们。如果有一天这是我们必须作的抉择,我希望我们知道当如何决定。肉身的失败,好过道德的失败;宁可失去言论、集会,甚至宗教的自由,而不愿在神面前丧失良心。因为在祂眼中,正直比自由更有价值。
恐怖主义的兴起
以上所论的,多半是有关核子武器的事,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亦与它相关。不过有人会说,二十一世纪一开始,我们所面对的冲突并不是各国之间互掷核子武器,而是恐怖分子的兴起,过去十多年,恐怖主义已然快速勃兴,许多国家,包括美国、肯亚、西班牙、秘鲁、印尼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英国都曾发生可怕的暴力,由不同背景的恐怖分子所策动。
如果说,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的崩塌,象征著受压迫的人得到了自由,那么,二○○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双子星大厦的崩塌,则象征著过去拥有自由的人正面对新的压迫。美国再也不能以为在领土内便可安稳无忧,当那两架客机故意撞入世界贸易中心,另一架又差一点撞到华盛顿的目标,恐怖主义一下子声名大噪,突然间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恐怖分子。二○○五年,伦敦也成了自杀炸弹客的目标,三颗炸弹在间隔五十秒之内,分别于三处伦敦地铁站爆炸,第四颗在巴士上爆炸,五十六人死亡,七百多人受伤。一九八八年泛美一○三班机遭炸毁,二百七十人死亡,而九一一事件是该事件之后,恐怖分子对美国人最厉害的攻击,而车站的爆炸事件则是伦敦自二次大战以来,伤亡最大的一次。
世界上发生许多暴力事件,但是透过新闻媒体,我们将其中一些列为恐怖主义。杰根史迈尔(Mark Juergensmeyer)在《藉神之名行恐怖:全教宗教暴力的兴起》(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: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) 一书中说,这些行动是「公然进行毁坏,不以军事目标为明显对象,而要造成广泛的惧怕。」
「恐怖主义」(terrorism)一词来自拉丁文terrere,意思是「让人颤抖」。因此,我们的反应也包括在该名词的含义里。换言之,恐怖主义的意义在于,它在受波及之人或目击者间所造成的颤抖,而不是单来自从事该行为之人。恐怖主义一向难以定义,不过所有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事实,即它最首要的特色乃是使用暴力,而这类暴力的目的和动机,往往不太明确。它和犯罪行为有所区别,主要是带有政治的理由;即便如此,许多恐怖分子也说不清楚,自己所行所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。
不过,恐怖主义的行为常造成无辜之人丧生,因他们多半是在事件发生时偶尔碰上的。这便意味许多人对这类恐怖行为毫不同情,间或使得恐怖分子发现,他们的暴力行为被公众或国际评论加以挞伐。爱尔兰共和军(IRA)或许可被视为恐怖组织,而他们已放下武器,接受政治解决方案,至于能否达成永久的和平,还有待观察。本书写作之时,著名的恐怖组织哈马斯(Hamas)在巴勒斯坦的选举中大获全胜,以色列拒绝承认其政权,这件事让国际社会陷入两难,因为巴勒斯坦需倚赖国际援助,经济才能运作。然而经援巴勒斯坦的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,少有几个乐意承认由哈马斯所统治的国家——如果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暴力,或承认以色列。这一幕要怎样解决,还有待观察。
近几年来,恐怖主义的发展带来可怕的结果,尤其是基地组织,在西方已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型运动,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全球网络,与最糟糕、最过分的暴力成了同义词。然而,对付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十分困难,比对付一个国家更难,因为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暴力,很难用传统的作战办法来反击。因此,一个军事力量极强大的国家,面对可能出现的恐怖威胁时,或许会作出过分的回应,美国与英国等国家,在九一一之后的反应,引起对这种反应的辩论。恐怖的行为与暴力固然要反击,策划者也应受公正的制裁,但是当布希总统称对九一一事件的回应为「反恐战争」,就引起了一场伦理的辩论——一个国家在宣战的时候,总要说明是在回应哪一种暴行。
当行动的焦点不再是寻找宾拉登,与对付阿富汗的基地组织,而是与伊拉克作战,使人不得不更加严重关切了。开战的主要理由,是他们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,但后来却发现似乎并非如此,虽然武器检验人员还没有完全清查这类武器可能的存放地点。并且,这项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合法通过,不过美国与英国连同其他的伙伴,却先发制人地开战了。这就让一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质疑,它是否经过合法的权威通过,而按照公义战争的原则来看,先发制人式的行为是否合乎公义。
不过,本书写作的时候,伊拉克已经展开选举,首次选出国会,正尝试在组织政府。支持军事行动的人说,倘若不是西方的军事干预,这样的民主选举绝不可能发生。这种说法是否正确?有人依旧认为,以外交手段或许便可推翻海珊和他腐败的政权,不必牺牲这么多人的生命。我们无法知道。许多伊拉克人认为自己得到解放,脱离了压迫,但有人认为,美、英等国的举动是一种别具用心的占领,因此便兴起恐怖活动的风潮,不单是伊拉克人,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投入。军事行动的后果至今仍有待判断,但我们必须期待,和平能临到伊拉克,新成立的政府能够秉公行义,所制定的宪法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人权。
恐怖主义的根源或许有好几种,其中有三个最明显。第一,西方认为现代化与民主的散播是不可避免的,也是可取的,但是有些人认为,西方世俗物质主义的散播,是对其他世界文化认同的一大威胁;小团体会感到全球化的影响淹没了他们独特的文化,以致这类团体采取极端的手段,宁可使用暴力,也要维护自己的文化。第二,经济的理由也很重要,全球化令人增加了提高生活水准的渴望,距离期待太远的贫穷人,有可能会对整个「系统」产生反感,因为他们看见,自己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生活。若是如此,恐怖暴力便是对全球系统不平衡的反击。持这种看法的人,将一九九三和二○○一年恐怖分子两次对世贸中心的袭击,解释为是在攻击资本主义的具体象征;然而,恐怖组织在策划并供应活动经费时,却常是透过全球经济体系的权力和效率来运作,这实在是一大讽刺。还有第三个,有时被称作「新恐怖主义」,其源头为宗教,又被称为「后现代恐怖主义」。这种恐怖主义很难用武力来还击,一个视死亡为殉道、期待在来生得奖赏的人,武力对他有何作用?这类与宗教牵扯在一起的宗教语言和行动,混杂在恐怖主义之中,被人利用来达到政治的目的。
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中,宗教暴力组织逐渐兴起。杰根史迈尔说,一九八○年代,美国国务院的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中,几乎没有一个是宗教组织,然而一九九八年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(Madeleine Albright)列出三十个世界最危险的组织,一半以上是宗教组织。其他人的分析数字更高,以致前美国国务卿克理斯多弗(Warren Christopher)评论道,以宗教与种族为名义进行的恐怖活动,已经成为「冷战余波之后,我们最大的安全挑战之一」。
由此观之,虽然恐怖分子自称其暴力活动是基于宗教理由,或是出于该宗教的命令,我们却不可将其他世界宗教视为魔鬼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基督徒不应当落入伊斯兰恐惧症,因为那是将伊斯兰教扭曲、定型,只会破坏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友好关系。不过,雷马强佐(Vinoth Ramachandra)在《信仰的冲突:多元文化世界中基督徒如何守正不阿》(Faiths in Conflict: Christian Integ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)一书中指出,这种挑战是相互的,宗教与文化会互相指控对方为魔鬼,采取防卫姿态,生怕对方会影响自己。中东许多文化尖锐地批评西方的价值观,甚至认为西方价值观以人权用语为外衣,要强加于人;可是,伊斯兰也应当避免军事性的「西方恐惧症」,有人称之为「基督教恐惧症」,这乃是对基督徒和基督信仰的曲解。雷马强佐评论道:
「伊斯兰恐惧症」、「西方恐惧症」、「基督教恐惧症」,这些名词很不中听,但尽管不讨人喜欢,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所有的恐惧症都是出于无知,同时缺乏对自我和自己所属团体反省的能力。西方基督徒和穆斯林若要建立良好的关系,基督徒必须率先破除西方人士反穆斯林的偏执,指出其中错误并予以斥责;而同时穆斯林领袖也要以同样的热诚,来破除在西方和在所谓「伊斯兰世界」(dar-ul-Islam)各自之间所存的偏执与仇视。
我们也需要记住,宗教煽起的暴力在全世界各个宗教里都曾出现,包括北爱尔兰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内,印度教的极端分子、犹太教的基要派都难以豁免。暴力并不限于个别宗教。
宗教煽动的暴力增加,也是一个信号,表明宗教的影响力在二十一世纪愈来愈强。身处于二十一世纪的欧洲,我们会误以为宗教在世界舞台上不再扮演角色,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宗教认同在全世界正益形重要,许多冲突正是肇因于此,冲突的双方各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怪责对方。例如,在波士尼亚研判冲突的本质时,宗教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种族或政治联盟。
恐怖主义在人的思想里能够扎根,似乎有一个必要的因素,即认定世界已经处于暴力状态,每个人都处在战争当中。要一个人以为自己投身于暴力是正当的,就必须让他有这个想法;世界处于暴力中,因此恐怖分子以暴易暴就振振有辞。同时,倘若国家看来软弱无能或一味妥协,不能纠正错误,暴力就有可以运作的空间。有时基督徒误以为他们的宗教是恐怖活动的理由,这就令他们更加认为,与其任凭当前的情势继续下去,不如让这样的活动达到目标来得更正当、更公义。美国的堕胎诊所遭人投弹,亦是如此。施暴者说,他们想借由除去世上的邪恶来引进基督徒社会,其实,他们的作法不啻卷入邪恶,并且使他们想要倡导的信仰蒙羞受辱。
这类行动多半似乎不是要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,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宣示。针对这点,杰根史迈尔说:「宗教恐怖主义的行动是种『象征』,我的意思是,它们的意图不在当下的目标,而是为要表明或论及某件事,例如,更大的征服,或比表面看来更可畏的奋斗。」
指认宗教煽动暴力要很小心,这点非常重要。某些权威人士可能会以讽刺的语气来讲论,以达到政治目标;而委身作「殉道士」的人,则可能会把这种行动本身当作目标;有些宗教暴力者或许存有政治目的,想要实现伊斯兰国度,有些行动也可能只是一种象征。明白这点很重要,我们需要深入探讨。
宗教引发的暴力,必须要从更深、更广的背景来看,许多时候,宗教暴力的背景是灵界的争斗:一场肉眼见不到的「宇宙」大战,正在我们周围进行。宗教暴力可以理解为与这更深一层的属灵冲突紧密相关,最明确的信号之一,就是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客相信,只要杀死伊斯兰的敌人,他们就会被接纳进天堂,并因此大得奖赏。我已经说过,自杀炸弹客的作法让人防不胜防,难以制服,而要胜过自杀炸弹客的幻想(以为这种暴行可以让他们进天堂),更是难上加难,如此的信念使这些人认为,无论是去炸高朋满座的餐厅,还是去炸挤满乘客的巴士,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有道理,有小孩在场也无所谓。
不过,对宗教这样的扭曲,反倒为促进和平的人提供了机会,委身于非暴力之人可以看出,这样的委身含有莫大的力量,甚至可能比藉暴力达到目标还更有力。凡是渴望和平的人都对暴力产生反感,这种感受足以跨越种种文化与宗教的藩篱,将人团结起来,组成相通的团体,互相尊重、了解。基督徒蒙召是有盼望的,知道个人可以改变,社会可以实践公义,我们相信,人们可以转离暴力,以拥抱和平为职志。为了这个目标,即使在暴力充斥的世界,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努力追求和平。
基督教的确也讲到宇宙大战,使徒保罗在致以弗所人的书信中说,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争战,乃是与「执政的、掌权的」争战。他劝告以弗所的基督徒,要穿戴「神的全副军装」,但是这些军装是指基督徒的美德和使命。例如,军装之一被描述为和平的福音,另一项是真理,还有一项是信心;这套军装的概念,与宗教暴力的残酷作战观念正好相反。保罗乃是在说,面对虚假的世界,真理与诚实是惟一的武器;面对暴力的世界,促进和平是惟一有效的抵挡方式。只有透过重新认识真正的基督信仰,才能制止宗教引发的暴力。
基督徒促进和平的呼召
耶稣曾论及战争与和平。一方面祂警告我们,将有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」;另一方面,在列举神国度子民的特色时,其中之一便是积极促进和平。祂声称,祂的门徒使人和睦,必受到神与神之儿女的祝福(马太福音五9),因为使人和睦是神的圣工,神透过基督与我们和好,又使我们彼此和好,除非我们也从事促进和平的工作,否则便不配称为祂的儿女。
我们可采取哪些实际的作法,来促进和平呢?
要促进和平,基督徒必须恢复士气
今日教会有两种趋势,令基督徒士气不振。两者我们都要坚拒。
第一个趋势是大事化小。我们面对挑战的态度偏向消极,漠视世界的难题,把世界缩减到只剩自己想要作的事,是很容易的。但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、百万人的受苦、我们生活方式的摧毁,是不容忽视的紧要大事。
第二个使我们士气不振的趋势,是对未来非常悲观,以致容许无助的情怀滋长。冷漠与悲观都不是基督门徒当有的态度,我们蒙召是要参与当代的文化,而非对它不理不睬;在绝望的文化中,当人们对改善的可能嗤之以鼻时,我们要能成为盼望的榜样。基督教会的声音一定要让人听见,不单在本地,更要在全国、在整个国际间;这就意味要透过媒体清楚表达我们的观点,并且一旦看见政府有必要改变,就必须加以劝服。这个世界需要激进的和平促进者。
要促进和平,基督徒必须祷告
请不要拒绝这个劝勉,视为无关紧要的敬虔。对基督徒而言,绝非如此,即使不论祷告的道理和果效,我们也奉命要这样行。我们的主耶稣特别吩咐我们要为仇敌祷告。保罗嘱咐我们,在聚会崇拜时,首要之事便是为国家领袖祷告,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地度日」(提摩太前书二2),然而今日「公众崇拜的牧祷常简短而公式化;所祈求的事毫不用心,陈腐老套,几近『无用的重复话』;而会众则在打瞌睡、作白日梦,而不在祷告。」我们非常需要在崇拜时认真代祷,为统治者与政府,为和平与公义,为朋友与敌人,为自由与稳定,也为能免于核子浩劫。又真又活的神必会垂听、应允祂子民认真的祷告。
要促进和平,基督徒必须建立和平的团体作榜样
神呼召我们,不单是「传讲和平」、「使人和睦」,也要实行出来。因为祂的目的是透过圣子与圣灵的工作,建立一和好的新社会,其中不再有帘幕、围墙或栅栏,而一切分裂的因素,如种族、国家、阶级、性别,都已荡然无存。祂要祂的教会成为祂国度的记号,亦即,从教会中显明,倘若人类社会在祂公义和平的治理之下,会是怎样的情形。一个真正属神国度的团体,就可以向世俗社会的价值体系发出挑战,并且提出可行的作法。倘若教会没有达到神要她成为的和好团体,就很难呼召全世界和平相处,倘若良善要从家里做起,则和好亦然。我们需要在教会、在家里完全废掉怨恨、忿怒和苦毒,使它们成为充满爱心、喜乐、平安的所在。有和平表现的团体来促进和平,影响力无与伦比。
要促进和平,基督徒必须为建立信任贡献力量
「建立信任措施」(CBMs,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)的概念不必只限于特定的军事行动,每当有人觉得受到威胁,基督徒的反应当为:努力除去恐惧,建立信任。我前面谈过需要「大胆的和平姿态」,而接下去则需要进行CBMs。无论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为孩子设立联合学校,或是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家庭聚在一起,分享文化,CBMs的作法对和平极其重要,个别的接触能除去歪曲的观念,彼此发现对方也是人,基督徒更应该外出旅行,去服事、去分享,在基督里认出彼此是弟兄姊妹。
要促进和平,基督徒必须鼓励公开辩论
倘若和平运动要对和平的促进有贡献,就必须努力推展充分运用资讯的讨论,无论什么时刻,总有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辩论。我们为何需要囤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?「拥有合乎道德,但使用却不道德」的立场是否实际,还是自我矛盾?所谓的「另一种国防政策」究竟是否存在?建立「传统」军队是否有利于减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,还是两者可同时削减?为保护国防而让千万平民赔上性命,是否合理?最终而言,国家的正直与安全孰重?这类问题,还有更多其他问题,都必须提出来辩论。
每一个基督徒蒙召,都要去促进和平。八福并不是八种选择,有些人愿作温柔的人,有些人去作怜悯人的,另有些人去使人和好;基督乃以整个八福来形容祂国度的子民。当然,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乌托邦,基督公义与和平的国度,也不会在历史中普及全球,必须等到基督再来,刀剑才会打成犁头,矛枪才会打成镰刀。然而,这事实并不容许我们去大量开工厂,制造刀剑与矛枪;基督曾预言会有饥荒,我们是否就因此不求将食物作更平均的分配?祂对战争的预言,也毋需成为我们追求和平的拦阻。神是主动和好者,耶稣基督也是主动和好者,因此,倘若我们要作神的儿女、基督的门徒,就必须去促进和平。
微读书城官网:https://wdbook.com/
下载微读书城App:https://wdbook.com/app